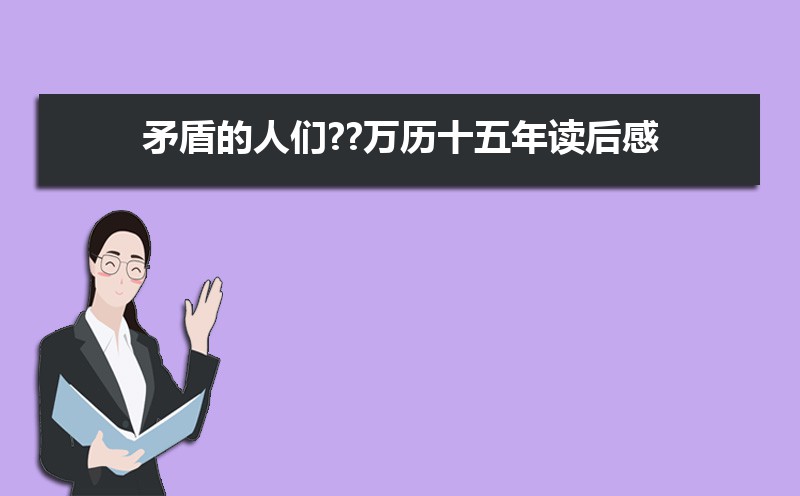二、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
皇帝的消极怠工,文官集团的涣散,使庞大的帝国相互掣肘、举步维艰,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这些问题到253年后的鸦片战争时依然如此,以致“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而在西欧,这一年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的前一年,到1840年英国已经处于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同为大国,为什么明朝的发展停滞不前,英国却能摆脱困局、实现强国梦想呢?
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在这里,反作用的力道太大了,大到似乎要颠倒规则。明朝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行政问题通过道德原则简化,以适应政府的低能;财税制度混乱僵化,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脱节。黄仁宇先生把这种管理状态下的社会结构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上层是文官集团构成的长面包,大而无当;下层是成千上万农民构成的长面包,没有有效的组织;上下层之间是尊卑男女老幼的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是明朝立国的根基。它们粗浅简单、保守僵化,缺乏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使货币税收、金融保险、交通通信、商业组织等先进制度无从发展,以致国家“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导致国家机构运行迟滞,上下层之间的沟通渠道堵塞,最终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凝固。这是中国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明清的主要原因,也是明朝走不出死胡同的根本原因。
贫瘠的土壤无法孕育高大的树木。在这个大环境下,制度建设成为水中花、镜中月。比如税收制度,每个县的税额自朱元璋时代固定下来,无论天灾人祸、人口变化均不增减,等到执行不下去发生欠税,将所欠税额按比例减免后征收,等于变相减税,各地争相效仿,欠税成为常态,导致国库空虚。再如军队补给制度,军队是国家武装,补给本应由中央统一调配,但明朝将军队补给交给地方负责。一个地方要给十几个卫戍供应钱粮,一支军队的补给也来自十几个府县。如此犬牙交错的供应模式无法充分保障军队补给,一旦行军作战更加难以应变。为适应落实的组织制度,军队作战只能放弃先进的主动战术,采用落后的被动战术应敌。还有公务员工资制度,中央规定的基本工资很低,各地就在税收之外征收“常例”“火耗”,给自己发地方津贴,而“常例”、“火耗”的征收又没有标准,等于地方变相拥有自己的财政权,还不受中央控制。赋役制度,可以称为吃大户,负责接待官员来往的驿站,使用的交通工具、住宿饮食摊派到当地的富户,家里越殷实负担越重,极大地限制了民间资本的积累。就连度量衡,官方与民间使用的都大小不同。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万历十五年》一书散发的强烈现实关怀,于常处凸现的深刻道理,对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仍不乏借鉴意义。
一是去道德化。弱化制度中的道德色彩,让制度成为可执行的行为导向。一方面道德是道德,制度是制度,莫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剔除制度中模糊性、性因素,加强技术性、规范性因素,减少不确定或模棱两可现象,避免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名不副实、被高高挂起的情况。另一方面道德拔高了对人的要求,使制度失去了现实意义,正如逼着朱翊钧做道德范本,他只能逃避;标榜官员低薪,就会出现税收之外的“常例”。要留下一个解决问题的缓冲空间,不要一下子上纲上线,使政府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的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二是去人格化。张居正是万历时期的精英人物,聪明才智堪当大用。他执政期间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如丈量土地、一条鞭法、官员考成法等。这些富国强兵的措施,整顿了吏治,充实了府库,夯实了军队,但随着他的故世全部付诸流水。这种人亡政息的现象令人扼腕叹息。因此,制度建设应注重连贯性、持续性,减少人为因素的色彩,使之不因领导个人方面的因素而存在或消亡、夸大或削弱,让制度拥有自己的生命。
三是去特权化。特权本身就是对制度的否定。如果说制度是一条大道,特权就是在道路上划出的一条快速通道,这条快速通道越宽,占用的道路资源就越多,行走在公共道路上的人就越拥挤。明朝的赋役负担由地方富户承担,但官僚大户享有豁免特权,真正负担落到中小地主身上,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