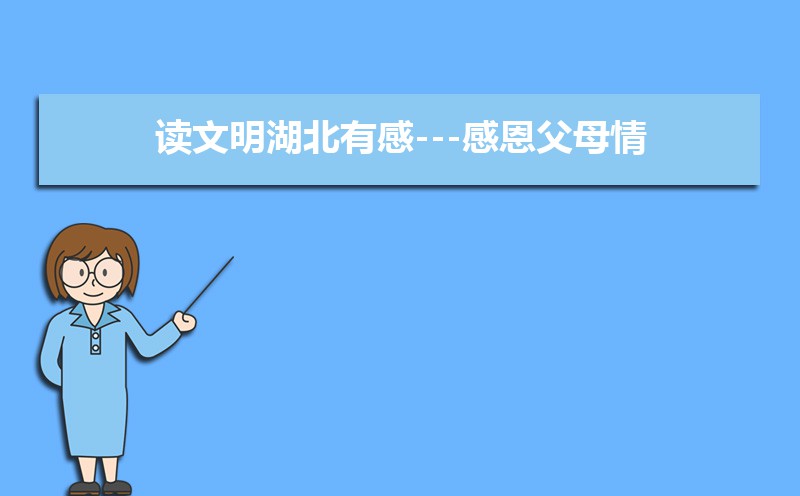读《地铁里的枪声》有感
如果你有浓厚的兴趣想要了解美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不妨拜读一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乔治·P·弗莱切(GeorgeP.Fletcher)所着的《地铁里的枪声》(ACrimeofSelf-defense)(陈绪纲范文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如果把它作为一本故事书来看,则它无疑是冗长而枯燥的;而作为一本法律参考书来看,则显得相当有趣。该书以极其细腻的笔触,从全方位的角度,描述了戈茨案的整个审判过程。当然,作者是试图以戈茨枪杀案一案的真实案例,通过站在不同的视点和角度展述和分析,到底案中被告戈茨是正当防卫还是持枪杀人?从而揭示法律的真谛:一纸陪审团的裁决和法院的判决,是否实现了真正的正义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司法制度成功地把公众的激情从复仇行为导入法律辩论的领域。但是,对我来说此书最有价值的是,通过作者对戈茨枪杀案从1986年12月陪审员预选至1987年10月做出初审判决的长达10个月时间的审判过程的事无具细的描述,期间夹杂了大量的法学届、社会各阶层的反应和充满思辨色彩的分析,仿佛是美国司法审判制度的一面三维显微镜,向我们清晰、详尽、全方位地透视了美国司法审判中的几乎每个方面。对一个意欲探悉英美法系司法审判制度的人来说,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该书首先从一个真实的案例展开: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公共秩序濒临崩溃,各种犯罪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不断上演。而地铁更成为纽约的"地狱",这里均每天发生38起刑事案件。对此,纽约市民心存恐惧却只能痛苦忍受。当其他人只是幻想着如何应对时,一个人却以开枪做出了回击。1984年12月22日,身材瘦弱的工程师伯恩哈德·戈茨(白人)搭乘地铁时,四个年轻人(黑人)靠了他并向他索要5美元。戈茨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手枪……四名年轻人受伤(其中一人送医院后不治死亡)。当社会的不公缺乏公共机构的解决,来自私人的复仇便满足了人们对秩序和公正的渴望--戈茨成为了大众英雄。但与此同时,他也面临来自法庭的审判。戈茨僭越国家维护法律和秩序特权的行为,究竟是正当防卫,还是持枪杀人?
在《地铁里的枪声》所及的众多视点中,我最感兴趣的便是英美司法制度中的陪审团制度,作者对此进行了极细微的描述,他甚至参与了陪审员的筛选。在这里,我们可以很难得地获取到关于从筛选陪审员到陪审团作出裁决的极其生动具体的详尽资料。
在戈茨案中,初步筛选陪审员的地点便位于离最接枪击发生地的一个地铁站--钱伯斯大街站不远的中心大街上的刑事法院大楼。筛选者是该案的法官(斯蒂芬·克兰法官),双方的律师,(www.creditsailing.com)一个法院案件报道人,一两个研究者,陪审员将从曼哈顿的居民中选出。作为筛选者,他们首先要考虑的便是,被作为筛选对象的、可能作为陪审员的公民,在来法院大楼的途中将路过报亭,可能会看到有关报道大众英雄戈茨的案件的新闻头条,到底会否因此而受到影响。从超过三百多个候选陪审员名单中挑选陪审员的程序一开始,他们就得到警告不要盲从公众对这个案件的评论意见,也不要跟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谈论这个案件。"他们被慢慢地带入司法制度的庄严职责中。最终作出裁决的权力将属于他们,也仅属于他们。"
筛选陪审员,首先要看他们是否有能力且愿意履行陪审员职责。他们的雇主会允许他们离开五到六周吗?他们是否会因此遭受经济、家庭、或职业上的困难?陪审员参加审判的规定时间只有两周,较两周更长的案件审判,则需要志愿者承担义务。如果他们愿意履行陪审员职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考察他们对被告是否太过倾向或过于反对。访谈将在相对比较私密的环境中举行,这样陪审员可以畅欲言,而不必使得其他正在等待的候选人感觉尴尬或受到影响。
筛选陪审团的目标,就是要找出不偏不倚和没有偏见的陪审员。不管在实际上能否实现,法律仍然相信这样的观念:陪审员裁决事实,仿佛他们并不透过自己个性的窗口看尘世。然而,在实际中,只有法官需要恪守对客观性的官方信念。律师们自然寻找那些偏向他们这一方的陪审员,但又不能太过,否则会遭到对方律师以偏见或理由提出异议而被剔除。在陪审团最后宣誓就任前,每一方都可以提出申请剔除某一陪审员,可以依据好的理由。在戈茨案这各类型的案件审理中,也可以不由分说地剔除15名陪审员,而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
戈茨案中,初步筛选程序从1987年年初至3月初才完成,留下来的135名候选陪审员名单,或多或少能够履行陪审员职责,或多或少不那么存有偏见。他们在3月23日回来接受第二轮筛选,也就是公开的审查。当陪审团筛选的公开阶段开始后,克兰法官向律师们解释了规则。18个潜在的陪审员将从大名单中随机挑出,将在陪审团席就座。克兰法官和双方律师向其提问,以诱使其表现出偏见,然后他们便到隔壁的法庭去一个个地考察陪审员。每一方都可以提出理由质疑和剔除一名陪审员候选人,如果克兰法官拒绝了该方的反对意见,这一方就得决定他们的反对是否足够强劲,而需要动用他们的15个绝对质疑反对机会中的一个。一般而言,克兰法官倾向于同意附理由的申请。如果某一陪审员通过了这一审查,他或她就可以进入12人的名单中。每一方都不得临时接受某一陪审员,而到最后阶段运用额外的质疑反对机会来重新剔除名单中的那一人选。
在陪审团筛选的关键阶段,被告戈茨聘了一位心理学家作为顾问,他的任务是帮助辩护律师根据最后的分析,更好地判断是哪类人,以及具体哪些人会视枪击为对刑事犯罪的防卫反应,而非看作是不负责任以及敌意的行为。他筛选陪审团的首要标准是某一陪审员是否会更可能认同犯罪的受害人,而不是加害人。
检察官筛选陪审员的标准则直截了当。他明显偏好那些未曾成为犯罪受害人的人。注意到案件中的政治因素,他倾向于那些理解携带武器的枪手在地铁里昂首阔步所带来的公共危险的人。他注意让遭到过抢动的受害人不要进入陪审团。但曼哈顿各区犯罪活动的受害人实在是太多了,很难找出一个陪审团对戈茨的困境是没有同情的。
由于被告与受害人属于不同的种族,在筛选陪审员时,还要考虑种族问题。为了澄清陪审员曾受害过的刑事犯罪的种族上的含意,克兰法官把每一个犯罪受害人叫到审判席前,询问加害他们的罪犯的种族情况,这样他们可以说话不会被其他候选人听到。询问这一问题的要点在于:考察候选人是否将种族歧视与对犯罪活动的恐惧联系起来。而美国各州法律对以种族因素排除陪审员的规定并不一致,根据当时纽约州的法律,被告可以有系统地把黑人(受害者种族)排除在陪审团之外,检方不能对这种歧视行使绝对质疑反对权。
总而言之,检方和辩方对于对方所要寻求的陪审员类型都有妙策,他们在挑选陪审员时经常要凭直觉作出判断。双方都充分利用筛选陪审员的过程中可以与陪审员直接讲话的机会接陪审员,跟这些拥有裁决权的人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教育他们一些将来会主导审判的道德和法律问题。每个人都参与到这个教育陪审团的过程中,法官和律师都要求陪审员表现出区分信息的相当能力。他们必须把他们自认为已经了解案件的情况,与他们在庭审中所看到和听到的证据分别开。在大部分教育陪审员的问题上,辩护律师、检方都与法官合作,形成统一战线,来维护已确立的原则以及法律上的区分。但相互竞争的双方律师不可避免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来与陪审员交流,以让陪审员们得到一些律师想让他们接受的观念。而法官则会警告他们在筛选陪审团的过程中对对方当事人使用贬称是不合适的。最后,当第12名陪审员确定后,挑选陪审团的工作就完成了。经过幸运式的抽签,他们的其中一人将成为陪审团的主席。
挑选陪审员的漫长过程结束后,提示案件事实真相的时刻--庭审终于来临了。4月27日,陪审员宣誓就职,控辩双方向陪审团做开庭陈词。然后陪审员便要在检方和辩护律师双方之间的唇枪舌战、互相攻击和律师自导自演的事实陈述之中分辩出事实的真相。律师还要对证人作证的顺序作出决定,并像导演那样在排练中指导这些证人,带领这些证人逐渐适应他们的角色。在庭审中,如果自己一方的证人不能表现出律师所期待的那样,律师是不能提示的,禁止提诱导性的问题。但在交叉盘问中有质疑之处时,律师是可以提诱导性问题的,他们还可以常常很傲慢地要求证人回答"是"还是"不是"。一般而言,辩护律师对交叉盘问比对直接盘问要强,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反击公诉方的证人。
在庭审中,陪审团将会看到检方展示的证据,如被告和受害人的供状录音和录像。这种证据大部分在庭审开始前都秘而不宣,除了律师和法庭官员外,没人看过这些录音带和录像带。甚至辩护律师也只是在庭审开始前不久,才知道所有那些证人是什么人。供状录音带是陪审团听到的对当时发生情形的最为详细的描述,录音带不仅复现了当时枪击的细节,而且也让陪审团对被告的个性有一个异乎寻常的洞察。供认状本身为辩护律师提供了辩论意见,以反击检方传唤的证人在案件的某些事实方面对被告方冲击的作证。
供认状是中立的,有待于对被告有利或者不利的解释和辩论意见,证人的作证也是如此。检方传唤了案发当时以及之后所有能找到的目击证人来作证,而不管他们的证词是否可能强有力地支持检方的公诉。一旦检方完成了他对证人的直接盘问,辩护律师就开始从证人中寻找对被告方有利的材料。当检方完成证据出示和对检方证人作证完毕后,提交证据的主动权转到被告方。
随着所有的证据提交给法庭,案件的主要争点便一目了然。陪审团要依据他们在庭审中所听见和看见的证据和辩论来作出裁定。他们无权在作出裁定的讨论时,依据他们在庭审前听到或读到的案件事实来裁定。在庭审进行过程中,他们被禁止了解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有很多材料他们不知道或者是本不应该知道。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是通过相关性和适当性法律规则过滤后提供给他们的。他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是些什么信息避着没让他们知道,以及原因何在。
陪审团审理既是一种高形式的民主,也是一种最赤裸裸的审查制度。陪审团对被告是否有罪表达出社会的声音,但同时,在庭审中,陪审团也不断遭遇法庭中的审查。有时候,这种审查就当着陪审员的面进行。双方律师走审判席,在法官那里私底下辩论。无论是复杂的,还是只是持续几分钟的辩论,陪审员得离开法庭,回到陪审团审议室。他们在那里一直等到被重新叫回到法庭,而不会被告知在他们离开法庭时,法庭作出了什么样的裁决。这种对于陪审团应该知悉哪些作证的辩论,反映了对抗制司法的精神。在欧陆的纠问式审判制度中,从未将最终的裁决权交给一群不懂法律的陪审员,他们对于庭审中的证据听审比较随意。而在对抗制审理中,律师大有文章可作。他们不仅向这些不懂法律的陪审员呈堂证据材料和说服他们,而且还必须对他们这一面案件事实所采纳的证据范围,动辄争来吵去。在这种辩论中所需具备的高超的法律技巧,对律师来说是一个挑战,同时也让法官作出数量惊人的法庭裁定。在戈茨案庭审中,克兰法官就作出了几百个法庭裁定。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下,一个初审法官表现自己权威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这些裁定来限定庭审中证据的范围,而这些裁定及相关辩论的内容都是陪审员未曾听审到的。
在陪审团作出最后的裁决前,他们还将听到检方和被告方的结辩陈词。经过两天双方的结辩,接下来克兰法官花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解释了责任的要素以及自卫的要素。
在经过历时46天的庭审后,陪审团最终在1987年6月12日退出法庭,到法庭后面没有窗户的审议室。在庭审的六周里,他们在这里打发了不少时间。在经过不能读报、不能看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也不能彼此交谈、或对他们的朋友、家人谈论每天所听审到的证据的想法等严格的纪律限制后,现在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交谈了。他们终于可以交流他们对被告是否犯罪的感受和想法了。他们得到一份多达13项的指控单,经过充分的讨论后,他们将要对分别每一项指控作出一个完全一致的裁决,无论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都必须是一致的意见。然而,一致的裁决并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甚至并不是必然可以得到的。在讨论期间,在遇到对证据的质疑或对法律问题的困惑时,他们可以通过陪审团主席向法庭递纸条,索看证物,甚至可以要求返回法庭重新听取有关证词,或由法官对他们作出授课式的指示。
在戈茨案中,陪审团经过了3天的讨论(期间的周日休息)后,于6月16日作出了一致的裁决:仅一项三级非法持有枪支罪名成立,有罪。
读地铁里的枪声有感
发布时间:2023-09-18 22:47:09
其他人推荐看
- 吉利学院江西录取分数线及招生人数 附-最低位2025-05-23 16:37:20
- 甘肃高考排名在99250的理科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2025-05-23 16:36:06
- 南昌师范学院和南京体育学院哪个好 分数线排名对比2025-05-23 16:34:41
- 江西高考排名在49850的理科类考生能报什么大学(原创)2025-05-23 16:33:06
-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是本科还是专科,属于什么学历类型2025-05-23 16:31:37
- 甘肃医学院在安徽录取分数线是多少?最低位次排名2025-05-23 16:30:22
-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陕西录取分数线及招生人数 附2025-05-23 16:28:55
-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在安徽录取分数线是多少?最低位2025-05-23 16:27:35
- 西行漫记读后感2023-09-19 20:08:30
- 读制度高于一切有感2023-09-13 08:29:27